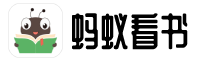我喜欢谢慎之好多年了。
我第一次见他,不过六七岁光景。
那时我随母亲去金山寺上香,母亲在前院听大师讲经,我坐不住,偷偷溜去后院玩。
我贪心摘池子里的荷花,不小心掉进水里,一个小沙弥将我救起。
我当时浑身湿透,袜上都是泥浆,一只鞋还丢了,整个人吓得不轻。
真奇怪,他明明穿着小沙弥的衣服,却束着发,竟然是个俗家弟子。他的衣裳也湿了,紧紧贴在身上,狼狈得很。
小沙弥把腕上的佛珠手串套到我手上,用帕子擦净我脸上泥沙,轻声叫我不要怕。
母亲身边的嬷嬷来寻我,大惊之下,抱着我道过谢便急急离去。
后来母亲辗转打听,救我的人是谢家三郎。
谢家三郎出生时天有异象,路过的修士说,他十九岁时,命中有一劫数。
谢家本没有当真,可那修士说的几件事后来都一一应验。
谢家老夫人慌了神,把年少的谢慎之送到寺庙,求高僧代为抚养。又请高人指点,传授一身武艺,只盼他能逢凶化吉。
我本是不信这些东西的。
六七岁的年纪,哪里能看进去佛经。
可是事关谢家三郎。
好心救我温柔的哥哥,怎能折在十九岁的大劫里。
旁的小姐放纸鸢扑蝴蝶的年纪,我日日泡在佛堂。我在佛前叩首三千遍,只求谢家三郎一生顺遂。
谢慎之十二岁那年方被谢家接回去,也是在那一天,太后下旨,赐婚云谢两家。
母亲不喜,自己的女儿早早被困住一生。
殊不知,我高兴坏了。
世间的女子,岂是想嫁哪个就嫁哪个?
而我却这般幸运。
谢慎之习武,他曾说过,等他一展心中抱负,海晏河清,便要与心上人策马游历河山。
他希望自己的妻子会骑马。
其实苏家的姑娘,大可不必学这些东西。
上京城里,也没有几个贵女会去学。
我的手上是缰绳勒出的茧子,腿上是被马腹摩出的血印。
我为学骑马,甚至摔断了腿。
听闻他喜欢性情坚毅的姑娘,我便强忍着,一滴眼泪也没有掉,倒是照顾我的嬷嬷眼泪掉了一筐。
谢慎之送我的佛珠手串断过一回。
掉得不巧,掉在庙会中,人流如梭。
我勾着腰在拥挤的人潮里摸索,一身白裙被蹭得不辨颜色,手上被踩了好几脚,踏破了皮。
身边的嬷嬷看情况不对,强行抱起我,几乎是拽着我回了府。
后来我再去找过,可惜一十八颗佛珠,只找回来十二颗。
我弄丢了救命恩人送我的唯一东西,母亲看我实在伤心,着人去寻了另外六颗差不多的给我。
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,旁人都瞧不出来不同,只有我,一眼就能分辨出那些细微的差别。
这些事情,我原打算等着洞房花烛夜讲给谢慎之听的。
可惜那是以前了。
母亲听说我了改主意,惊得失手打翻了茶盏。
「你怎可嫁他,谢家大郎,他……他岂是良配?」
不怪母亲有这样的反应。
谢家大郎谢妄之,以心狠手辣著称。
他是锦衣卫指挥使,天子近臣,享巡查缉捕之权,执掌诏狱。
而诏狱,是比死更可怕的去处。
被锦衣卫盯上的人,少不得要脱一层皮,没有人能从那里完完整整出来。
朝中重臣,皆对谢妄之忌惮三分。
谢妄之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婚娶,曾有女子故意泼湿他的衣裳,借故亲近,却连他的身也没有近,就被谢妄之反手卸了胳膊。
整个上京城,从来不见他对哪家姑娘多看两眼,也不曾出入风月之地。外界有传闻,谢家大郎根本不近女色。
更何况,谢妄之虽是长子,却是庶出。他长我十岁,我还在学认字的年纪,他已经满京城拿人办案了,是以这桩婚约一开始,没人往这方面想过。
母亲顾不得其他,紧紧盯着我的眼睛。
「云儿,你同娘说老实话,是不是那个谢三郎同你说什么了?这些年你做的娘都看在眼里,若是谢三郎对你做了什么事,娘决不轻饶他!」
我反手握住母亲,「谢慎之没说什么,是我自己想通了。他确实对我有救命之恩,可惜我们有缘无份,他的心不在我身上。我若是强行嫁给他,以后少不得夫妻生分。况且——」
我扭过头去看父亲。
「况且,同谢妄之成婚,对我们苏家大有好处。」
大概是我的眼神太过坚定,长久的沉默后,父亲缓慢道:「你决定了?」
「决定了,再不更改。」
本以为这桩婚事还要再拖一拖,太后突然病重,圣上为了叫太后高兴,想起太后早年赐下的一件喜事,朝散后,专门同父亲和谢家老太爷提了提。
半月后,谢家把聘礼送到了苏家。
谢家这礼下得极重,整整六十四抬,前厅没放下,甚至有部分抬到了后院。
我院子里的丫头满脸喜色。
「六十四抬的最高规格,小姐,姑爷当真对你上心呢。」
我看着满屋满院的大红色,心里面清楚,谢妄之于我交情泛泛,不过是皇家赐婚,不得不体面而已。
只是我有些好奇,不知道谢慎之最后是怎么同他大哥说的。
婚期定在三月后。
我没有再见过谢家三郎了。
听闻崔三娘的两个兄长,手痒难耐,又在外头赌钱,打着谢慎之的名号,赌坊也不曾为难他,只是把欠条,大张旗鼓地递到了谢府门口的石狮子嘴里。
这事最后怎么了结的我不清楚,只知道崔三娘的面片汤铺子不再开。
谢慎之给她另寻了间别院住着,一日三餐有人伺候。
我一听见就觉得不妥。
我和崔三娘只见过一回,她上来第一件事,就是与我说,铺子租金的事情。
显然她心气高,很在意那些,说她勾引依附谢家三郎的流言。
叫她真应了那些流言做金丝雀,恐怕她和谢三郎要起争执。
可惜这些事情与我无关了。
我自绣我的嫁衣。
天气日渐回暖,宋国公家的小姐与我自幼相熟,她快过生辰了,约我去城南的珠宝阁挑一些首饰。
莫说母亲,宋若惜对我转头与谢妄之议亲也倍感好奇。
苏家嫡女与谢家大郎议亲,虽然都是谢家人,但毕竟,之前坊间传闻,苏家中意的人选一直都是谢家三郎。
一路上,宋若惜几次三番欲言又止,眼神直往我身上瞄,我瞧她实在忍得辛苦,忍不住道:「你问吧。」
她果然问出那个问题。
我该怎么作答。
说谢慎之不爱我,我嫁过去,不过磋磨自己。
还是说谢妄之在朝中权势更甚,我嫁过去,对苏家大有好处。
想了想我,我违心道:「实不相瞒,我钦慕谢家大郎已久。」
时有锦衣卫办案,一队人马疾驰过去,当先一人,胯下一匹黑马,衣上暗绣飞鱼锦纹,腰缠一柄绣春寒刀,面容冷峻,神色淡漠。
正巧是他。
我哑了嘴,心跳漏一拍。
宋若惜似是没有看清刚刚驰马过去的人是谁,尘土飞扬,她掩住口鼻轻咳两声,小声埋怨起来:「好端端的,遇见这群活阎王,不会又要去哪里抄家吧。」
顿了顿,她又想起刚刚的话题,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
「你对谢家大郎倾慕已久?这事我怎么不知道?什么时候的事?」
我双眼望天,脑袋空空地编着瞎话。
「……去年中秋皇后娘娘的宴会上。」
「咦,谢家大郎去了吗?我记得谢大人不是从来不参与这些事么?」
我干巴巴肯定道:「有的,只是你忘了。」
四月初,我同谢家大郎完婚。
婚事很隆重,说不遗憾,却也不可能。
毕竟我想这一天想了很多年,母亲给我梳头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怔然,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,在那个世界,没有崔三娘,我同谢慎之白头偕老了。
鞭炮声震耳欲聋,烟雾弥漫处,人声鼎沸。
上花轿前我没看准,一脚踢在门柱上,险些摔倒。从旁伸出一只手来,极快扶了我一把。
我望向身侧,隔着盖头,只看到影影绰绰一个模糊的身影。
我低低向他道谢,四周太吵了,也不知道他听到没有。
谢妄之是庶出,他的生母已经去世,诸位兄弟中,他最年长,又在朝中担任要职,是以早早地从谢家分出来,另居别院。
但既然是成亲,少不得要回谢家主家去认认诸位亲戚,给谢家老太爷敬一杯儿媳妇茶。
盖头被称杆挑起,先是一张薄唇,掠过高鼻,我抬起眼,不期撞上谢妄之的视线。
其实我见过他很多回了,大多数时候他行色匆匆,腰戴佩刀,我只能略略瞥上一眼,像这般近距离细细地看,实是头一回。
谢慎之清冷。
而这位谢家大郎,虽与他三分相像,眉眼却要凌厉许多。大约是做锦衣卫,浸在血里太多年岁的缘故。
周围起哄的人太多,我无端红了脸,对谢妄之羞怯一笑,他怔然,然后慢慢也回了个笑,眉宇间的戾气便如烟消散开来。
这婚事盛大,前来观礼的人也多,我听见有宾客抽气,暗叹新娘美丽。
苏家嫡出的女儿,自小养在掌心,仪态气度,比起皇城里的公主也不遑多让,大婚之日,自然该是最光彩照人的那一个。
谢妄之引着我,一一见过谢家众人,我跟在他身后半步之遥,一回身就够得着的地方。
我很久违地见到了谢慎之。
谢家三郎,即便扎在人堆里,也是翩翩如玉的公子,一人就叫人认出。
周遭看热闹的人很明显的安静了一瞬。
我和谢慎之的事,京中也偶有流言,大家都在看我,以为我会失态。
他们低估我了。
无论如何,以后是我同谢妄之过一家,怎会叫人此时看了半分笑话去。
我脸上挂着浅浅笑意,同谢慎之见礼。礼数周全,如同初见。
「三弟。」
谢慎之的面色算不上好,没甚笑意,但转念一想,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爱笑的人。
他叫我:「大嫂。」
谢妄之不知何时握住了我的手,我更用力地回握他。
如此,我与谢家三郎,再不相干。
同谢妄之的婚后生活很平淡。
他忙于办差,不常在家。
府里的大小事务,一切交给我打点,有些事我拿不准,问过他的意思,他只说按照我的想法办就好。
说来谢妄之回家的时日确实也很少,我顺手在土里埋下几颗瓜子,他回来时,已有一片向日葵迎风招展,脆生生的鹅黄,朝气蓬勃地立在春日里。
再往后他出去办差,回来总会递给我一个小锦囊,里面是各地的花种。京城的水土与别地不同,不保证都能活,我尽量养。一整个春天过去,园圃里发起一片花苗,我再搭个篱笆架子,想必来年春天,架子上会爬满牵牛。
我们没有圆过房。
不知道是否应验了京城里,他不近女色的传闻。
但我隐隐有另外一层顾虑。
我和谢家三郎的事,他不可能不知道。我说我放下了,旁人又能信几分。
可是这种事情,谢妄之不说,我又怎好主动开口。
谢妄之是一个警惕性很强的人,近身的事,不喜欢下人来做。
有一回他要去京郊办差,郊外十里有驿站,虽说去不了几天,但总归要打点行囊。
我站在旁边看他收拾衣裳,终归没忍住,去找了一把伞塞给他,说道:「带上吧,过两天要下雨了。」
他抬起头,略诧异地看了我一眼,然后接过了那把伞。
两日后果然毫无征兆下起大雨,谢妄之办差回来,说起手底下几个人,被淋得狼狈,最后借了农家的屋檐躲雨。
「你怎么知道会下雨?」
我笑眯眯地望着他。
「你猜?」
谢妄之望向我,眼里隐隐有探究。
是夜我睡前沐浴,浴桶里的水极热,我叫丫鬟掺点凉水。
谢妄之的身影映在屏风之后。
「你身上有旧伤,该多用热水驱寒。」
我从未在沐浴时见过外男,大惊之下猛地蹲进水里。
水太烫了,我倒抽一口冷气,又不好立时站起来。
混乱之中似是听得谢妄之轻笑,再抬头看,屏风处空空如也,他已经走了。
那之后每天晚上沐浴都是略烫手的热水,只是不像第一回那样灼人。
九月底谢妄之受了重伤。
他是被手底下人背回来的,宫里的老太医来瞧了,说是再过两寸,就要伤及肺腑,得亏谢大人命大。
屋里血腥味太重,我搬了两盆茉莉摆到窗口,因为怕他半夜烧起来,我整夜都守在他身边。
谢妄之再醒来的时候,房中有茉莉清香,晨曦的第一束光照在被子上,是淡淡的浅金色,挠得人心里暖意沸腾。
我注意到这一切是因为我在发呆。
我熬了两个通宵,头昏脑涨,完全没有谢妄之已经醒来的念头。
我甚至,清醒又混乱地跟他问候了声早上好。
傻得很。
他也不说话,就静静看着我。
直到过了半刻钟,我才反应过来,手忙脚乱地给他倒水,又问他是什么感觉。
谢妄之叫了我的名字。
「阿云,你憔悴许多。」
太医说谢妄之要静养,伤好之前,切忌下地行走,更勿动怒。
他大概许多年没有休过这样长的假。手底下的人不敢来烦他,每日只捡最紧要的事来禀告,薄薄的两页纸,一会儿就能看完。
闲着的时间,他就半倚在那里,瞧我看账本管家。
有一天大抵是很无趣,喝茶的间隙,他问我:「以前你腿断了的时候,躺在床上都做什么?」
我想了想,回道:「念佛经。」
谢妄之侧了侧身,说道:「那念一段吧。」
我念了《观音经》里面的一小段。
念完以后谢妄之问我:「你很喜欢礼佛么?」
我实话实说:「不喜欢,我一直都觉得很枯燥,只是这么多年下来,习惯了。」
既然话说到这里,我索性跟他提了谢慎之。
日子好也是过一天,差也是过一天。总归我要跟谢家大郎长久过下去的,并不想同他因为这些事生分了。
我第一次跟他谈起他的三弟。
学骑马的事,学佛经的事,找珠子的事,那些谢慎之都不知道的事情,没想到最后,我竟然是同谢妄之讲了。
他安安静静地听自己的妻子讲另外一个男人,神情很专注。
我同谢妄之道:「其实一开始知道他和崔三娘的事情,我还是很怨恨。凭什么呀,我这么些年,拼了命活成他喜欢的模样,到头来,他却根本不爱我。」
「到后来,我想通了,站在谢慎之的角度,他又凭什么要因为我的付出喜欢我。这些年,礼佛磨平了我的性子,学骑马可以游历河山。虽说是为了他,讲到底,都是长在我身上的本事,说起来,我还要多谢他。」
「我年少时不知事,错把救命的恩情当作爱情,现在想一想,谢家三郎是个好人,凭谁掉下泥潭他都会救。这跟我是男是女,是美是丑没有关系。」
「我爱上的,或许不是谢家三郎,而是倾注在追逐他身上的那些时光。蹉跎这若干年光景,皆是我庸人自扰。」
讲到最后我眼角有泪,又带着些终于说出来的释怀。
谢妄之同我招招手,叫我过去。
他把我掉下的一缕发顺到耳后,低声道:「等我伤好了,我们去骑马好么?我养了两匹小马驹,是双生子,等我伤好了,它们也长大了。等明天,我叫人牵来过给你看看。」
我惊喜地望着他,谢妄之不自在别过脸去,握拳轻咳了一声。
我恍然,「哦,你是不是伤口疼,我去看看药熬好没有。」
走过回廊,拐角处,放了两卷字画和一支人参。
我叫来当值的下人,那小厮大惊:「怎么,三公子没提进去么?」
「三公子?」
「对啊,刚刚三公子拿来这些东西来,说要来探看大公子的伤。」
我朝外面望去,只见一行燕子飞上屋檐。
哪里还有谢家三郎的身影。
崔三娘的两个兄弟死了。
死在金陵城门外的荒地上,死状凄惨,尸身被乱刀砍成几截。
上次石狮子的事一出,谢家老太太发了话,要这两个人滚出京城,别给谢家抹黑。金陵城是谢慎之安排他们去的,谢家在那里没有根基,谢慎之托朋友给他们寻了差事。希望他们少了谢家这棵大树,能在金陵痛改前非。
然后总是事与愿违,崔氏兄弟到了金陵,反而变本加厉,出入赌场妓院,好不快活。谢慎之的那个朋友被追着要债不胜其烦,曾经几次写信给他,早已经是不耐了,
宋若惜有远房娘舅在金陵做官,是以早早得了消息。信末她问我,「你说,崔三娘要是知道这件事,会怎么样?」
倘若我是谢慎之,自然要瞒得严严实实。
可到底还是被崔三娘知道了。
崔三娘到衙门前击鼓鸣冤,状告谢家三郎,买凶杀人。
此事一出,京城哗然。
上京城里养外室的公子哥很多,被反咬一口把自己玩进去的,谢慎之算头一个。
就连母亲也来信与我,幸好最后嫁了谢家大郎,不然真是没有一日消停。
这件事未必就是谢慎之做的,崔氏兄弟在外结的仇不少。即便就是谢慎之做的,崔三娘一个小女子,又如何能告倒谢家的公子。
我问过谢妄之。
他说倘若我想知道真相,可叫锦衣卫去查。
我想了想说不用。
真相不在我,在崔三娘如何相信。隔了两条人命,只怕她和谢慎之,难以善了。
再见到谢慎之是在某次谢家家宴。
席间二嫂起兴,当场抚琴,我以萧声相和。
落座时,谢妄之已经给我剥好一碟蟹肉。
谢家祖母看了,颇为感慨。
说起当年,她与我祖母,是顶好的手帕交,只是各自嫁人生子,跟着夫君辗转谋生,联系便渐渐少了。想不如今到老,竟然又成了儿女亲家。
谢家祖母讲到最后默然垂泪,又提起儿孙都已成家,唯有最小的孙子,谢慎之还未婚娶。
她催促谢母,尽快给谢慎之议亲。
祖母年事已高,底下人又有意瞒着,她不知晓崔三娘那些事。
可是满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,谁家愿意把好姑娘嫁进来做谢家三夫人。
听说谢母已经偷偷在外地相看女子。
一顿饭吃到最后,众人各怀心思,气氛压抑。谢慎之更是只吃了两口,就借故离席。
是夜,下人来通禀三公子求见的时候,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这个时辰,我钗环都卸了,怎好再见外男。
我打发人出去拒了,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
可是跑腿的小厮说,三公子执意不走。
想想终归是自家兄弟,许是有什么要紧事。我一边穿衣裳,一边派人去通知谢妄之一声。
谢慎之面色泛着不正常的红,显然是离席后在外面醉了酒。他清瘦许多,崔三娘应该跟他闹得很厉害。
深夜前来,已然不妥,更何况是这般,堵在我的门前。
有丫鬟壮着胆子上前请他退后,谢慎之垂眸片刻,而后抬起头,眼中竟已含着泪。
他终于后悔。
他颤声道:「我和崔三娘……我不过是怜她孤苦……」
想来那日我同谢妄之讲话,该是被他听到。
我拢着袖看他。
「跟我没关系了,」我说,「你没有必要和我解释。」
谢慎之张口,千言万语,最后吐出苦涩嘶哑的一句抱歉。
抱歉什么呢?
我曾在佛前叩首三千替他许愿,也曾被马缰割出血痕。
但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,与他无关。
我冲他摇摇头。
「你并不欠我。」
谢慎之,你并不欠我。
想起他命里有大劫,我叫人去架子上把那串佛珠取出来交给他。
「你当年救过我一命,虽说事后我母亲也曾到贵府上去答谢,但一些金银俗物,终归表达不了我心里的感激。倘若你日后有什么需要,我们苏家,在朝中多少也说得上话。便是我夫君,在外面也有些人脉。有用得着的地方,你说一声就行。」
「这串佛珠我曾供在佛前许多年,希望能保你平安。」
谢慎之呆呆地望着那串手串,心腔仿佛被一只大手用力握住。
他苦笑起来,眼中满是酸涩。
「我宁愿你恨我。我们……我们本该……」
谢慎之欲上前,身后突然插进来清清冷冷的一道声音。
「三弟。」
谢妄之养病久了,总是一副闲散的样子。
现下他垂手站在房檐下,衣服袍带上下翻飞,眸中厉色摄人,我忽然想起这个人,是我们大靖的锦衣卫指挥使,执掌诏狱,心思深沉。
「她如今是谢家大夫人,你深夜找你大嫂有什么事?」
谢慎之含恨道:「倘若不是我一时糊涂,这桩婚事,又岂会轮得到你?」
谢妄之站到我身前,面含警告地睥他这个幼弟,冷冷地拍了拍手。
「三公子喝醉了,来人,送他下去休息。」
谢慎之挣脱要搀扶他的侍从,声音几乎带着哭腔。
「大哥,你是庶出,幼年时我母亲对你多有苛待,我做错了事情,往往也是你替我受罚……母亲说叫你替了这桩婚事,以你今日权势,怎会再听我母亲的话……」
「你是自己也想娶苏小姐吧……」
我蓦地看向谢妄之。
他挡在我身前,看不清表情,只听见他笑意讥讽。
「是又如何?」
「还要多谢你啊,三弟。」